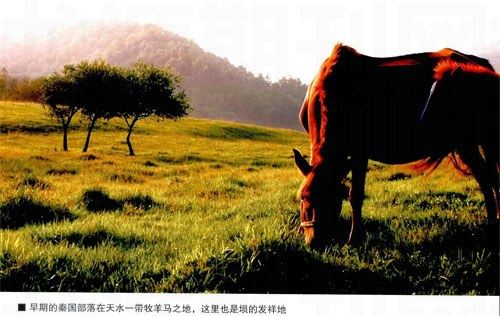 人物的口吻、情緒、性格,憑借自身對故事情節中人物形象的感悟和理解領會程度,用不同的姿態動作和面部表情神態來表現故事內容。
人物的口吻、情緒、性格,憑借自身對故事情節中人物形象的感悟和理解領會程度,用不同的姿態動作和面部表情神態來表現故事內容。
所以,聽一支小曲,猶如看一出大戲。
據說,上世紀五六十年代,秦安興國鎮一帶的老藝人張耀庭、閻光賜多次應邀赴蘭州獻藝,合唱的曲子《滿江紅》和《賞月光》大受歡迎。后來,1 957年秦安郭嘉鎮藝人到北京演出小曲連綴的蠟花舞,獲全國民間藝術第二屆觀摩會演二等獎,并應邀拍攝了紀錄片《萬紫千紅》。這些老人,不知道至今健在否?如果健在,他們也并不一定知道秦安小曲赫然入選2008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吧。
前幾年,我去郭嘉鎮——也就是秦安小曲和蠟花舞流行的地方。在街口,聽到一個老人在一棵大槐樹下引吭高歌。后來,我特意打聽到了那一段詞:
此處好風景
冬嶺秀孤松
每日間深山苦用功
忽聽得哪里響琴聲
鐘子期站在高峰壓頂
他撫得江湖河海水秀山清
又撫得綠柳桃花花……
老人用的純粹的秦安方言,只有一段,僅是唱辭,沒有對白,旋律迂回,一波三嘆。而且,這些詞多好呀,恐怕現在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也未必能寫出如此絕美的句子。據說,秦安小曲至今留下了四十余個曲牌,傳統曲目有《皇姑出嫁》、《八仙慶壽》、《薦諸葛》等幾十首。如果,在一個偶遇的下午,這位已經年邁的老人能夠手拿“摔子”,敲擊節奏,附之以一把僅有的三弦為其伴奏的話,把這些曲目一一唱完的話,我可能不會相信,我怎么能從二十一世紀的小村子里,一下子跌進了民國年代的秦安。
聽到這段小曲時間不長,我看到了一則秦安小曲的消息。消息稱,已有人給小曲賦予了時代的新意,將其搬上了戲曲舞臺,并召開經驗交流座談會,且得到省市領導高度重視云云。我真不知道,這個時代的人們,都在忙什么呀!藝術需要發展,但藝術也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。一些本源于大地的藝術,是對大地的饋贈,當我們將其從大地上連根拔出的時候,它還能存活下去嗎?
我想,即使我們為其供足氧氣,使它活著,也一定是蔫的。